在過去的五年時間之內,從2010年到2014年,工程顯示市場經歷了一系列的變革。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以來,進入一個整體性的成長低速期。不過,這一局面正在隨著2015年全球經濟形勢的新變化而徹底改觀。
筆者認為,2014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的直接刺激和政府直接投資等托市、提振手段的應用,正在開啟一個“工程顯示”的黃金時代。
新經濟調控手段的全球應用,驅動工程顯示需求增長
12月30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所在執政黨自民黨提議,日本應在2年內將企業所得稅下調3.29%,以鼓勵企業提高員工薪酬并加大投資力度。這是安培經濟學新的一支箭。下調企業稅自然意味著政府收入減少,這與2014年初提升消費稅的“穩定中央財政負債表的積極作用”恰恰相反。
筆者認為,安培新政的核心是“以量化寬松”為核心的經濟刺激政策,已經事實性破產。對于日本經濟,超發貨幣、貨幣貶值,自然能促進出口。但是,別忘了,日本是典型的資源和農業進口國家。量化寬松政策也會導致居民消費成本的增加。2014年,量化寬松和消費稅增加,已經成為日本經濟內需消費增長的最大空頭因素。
2014年,美國也正式退出了量化寬松。歐洲的政策還在緊縮貨幣與量化寬松之間游移不定。自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奉行的“量化寬松”工具,已經適時的被剔除出了“最有效經濟刺激”政策的一攬子方案。為什么呢?
答案主要在于以下兩個方面:其一,量化寬松雖然能改善社會經濟體的財務表,但是卻也能惡化貨幣發行單位,或者說政府的財務表——兩部分的作用哪個強、哪個弱沒有定論;第二,改善的貨幣供給和經濟主體的財務表,不一定就傳導到實業領域:例如,美國量化寬松最大的受益者是股市——18000點的新高說明了一切。在這里面,主要的經濟學說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資本追逐的是利潤,是最大利潤、是最便捷的利潤通道——顯然,實體經濟目前的利潤水平和便捷度已經決定了,實體經濟不會成為“量化寬松”貨幣的流入首選。
那么,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后量化寬松時代”各國政府的經濟刺激手段會是怎樣的呢?答案非常明確:越來越傾向于直接投資。這樣的一個事實說明了08年后我國政府在應對經濟下滑過程中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正確性,以及西方政策的局限性。2015年,中國、美國兩大經濟體的刺激手段將主要集中在能直接形成實體投資的領域;同時,歐洲和日本的經濟發展也必須依賴于一系列的直接驅動實體投資性手段;第三世界國家、興新經濟體也在表現出越來越強的直接投資驅動經濟的政策趨勢。2014年第三季度,國家發改委批準的歷史新高的“鐵路”項目,既已說明驅動實體投資的政策正在成為國家經濟調控的優先工具。
用實體投資代替貨幣的量化寬松的直接好處是既可以創造就業、又可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也有利于擠壓金融市場的泡沫效應。這一政策出現的原因,除了量化寬松政策自身的破產外,還包括“全球通縮”局面的形成。
2014年以來全球大宗物資價格下降:石油只是其中最核心的關注點。在石油價格走低之前,石油化工產業的主要制成品乙烯的價格已經持續走低半年時間。同時,煤炭價格也長期低位運行(國內大型煤炭企業2014年幾乎悉數有過虧損經歷)。此外,鐵礦石、銅礦和鋁礦石也處于價格低迷階段。鋁礦石的價格下降是中鋁2013年以來業務虧損的核心原因。鐵礦石價格下降是中鋼集團2014年危機的核心導火索。不僅是工業門類的大宗產品價格走低,農業大宗產品,小麥、大豆、玉米也處于相對的歷史低值階段。
國際大宗物資價格下降的原因主要包括:供給過剩、需求疲軟和美元升值。尤其是2015年,美元繼續升值和美聯儲加息的預期,更是推高了本已經嚴重的全球“通縮”狀況。對此,國內市場的反映既是,2014年12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1.5%。至此,2014年全年全國CPI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上漲2%,創下近四年CPI年度漲幅的新低。
通縮代替通脹成為全球經濟最擔憂的一件事情——這符合歷史上,大多數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先通脹后通縮的規律:通脹期可以視為是經濟危機的發展期,通縮期既可能是經濟危機的結束期,也可能是深化期。2015年,尤其是資源輸出國家因全球通縮遭受到的購買力損失和內部經濟問題將非常嚴重。這將形成全球經濟力量重新分配的基礎。對于美國而言,其希望的就是美元資本回歸國內,并促進投資實業。其他經濟體也渴望新鮮貨幣直接投資實業領域。2015年,全球經濟危機新一發展階段的基本形勢,將比此前更為嚴峻。因此,目前已經到達需要實施政府主導的,更為直接的、驅動實體經濟投資的穩定和刺激計劃的時候了。
通縮預期必然加大全球經濟的前景的不確定性。但是,上面已經提到量化寬松推高了印鈔部門的債務表。量化寬松手段已經走到盡頭。那么直接投資性,或者撬動直接投資的杠桿手段就成了最佳選擇。同時,大宗產品價格走低,也有利于各國低成本的基礎設施和實業投資建設。就國內而言,升級型先進制造業、新能源、交通、“一路一帶”沿線、社會管理、社會公共服務、基建和建材、高端加工和電子信息化產業都將是直接受益領域;同時,新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結合國際資本爭奪戰,也將為金融產業的改革和發展提供難得的歷史契機。而以上這些行業的發展,無一不需要“工程顯示”產品和技術的支持。
總之,2015年全球、以及國內經濟調控必然向直接投資和撬動直接投資的杠桿手段傾斜。一波新的實體投資高潮的到來已經不是藍圖,而是“在路上”。對此,工程顯示行業可曾記得“2009年后”四萬億刺激計劃帶來的行業成長盛宴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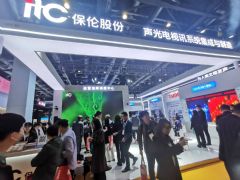







 Vtron威創拼接墻
Vtron威創拼接墻 臺達拼接墻
臺達拼接墻 飛利浦液晶拼接墻
飛利浦液晶拼接墻 aoc
aoc cisone啟沃
cisone啟沃 WAP手機版
WAP手機版 建議反饋
建議反饋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微信掃一掃
微信掃一掃 PjTime
PjTime